证据充足法官不秉公断案怎么办?
一、证据充足法官不秉公断案怎么办?
证据充足法官不秉公断,当时人应诉上级人民法院。检查院应及时提出抗诉,追究法官的责任。
二、机器人可以代替法官吗?
根据现有的信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人工智能(AI)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协助法官进行案件的审理和管理,但它不能完全替代人类法官进行裁判。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法官处理一些较为简单的案件,尤其是那些具有清晰事实和有限法律关系的案件。在这些情况下,AI可以通过分析大量数据并从中找出裁判规律,生成格式化的裁判文书。
然而,对于那些案情复杂、法律关系不明确或双方争议较大的案件,人工智能的能力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些案件通常需要法官具备高度的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以及能够在个案中进行深入的法律分析和判断,以实现公平正义的目标。
此外,人工智能的设计是基于固定算法的计算过程,这种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限制。在面对新的、未曾预见的情况或问题时,人工智能可能无法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因此,即使是在辅助性的角色中,人工智能也无法完全取代法官的地位。
从法律角度来看,任何形式的自动化都不能代替人类的独立判断和道德选择。法律职业被认为是不可替代的,包括法官、律师等法律职业人在内。
最高人民法院也明确指出,无论技术发展如何先进,人工智能都不允许代替法官进行裁判。人工智能提供的辅助结果仅可以作为审判工作或审判监督管理的参考,确保司法裁判始终由审判人员作出,并且裁判职权始终由审判组织行使,最后由裁判者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虽然人工智能在某些方面可以对法官的工作产生影响,但在关键时刻,如作出裁决和做出独立的道德选择时,仍然需要人类法官的主导作用和独立判断。
三、想问法律人一个问题,对于机器人代替或者部分代替法律工作者尤其是法官和律师,你们持什么态度?
“人工智能”确实会给法律行业带来很大的冲击,但就目前以及可预期的未来看来,并不会带来“根本上”的冲击。
问题描述中所谈到的例子其实只是“司法”,是法律这个领域中的一部分,尽管是关键的一部分。人工智能能不能辅助司法、提供裁判效率与准确率?是能的。基于最高法做的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库),各地法院(杭州法院比较领先)都在做司法+人工智能,各大律所也在研究自己的人工智能法律产品(比如天同所)。但这些产品都是在干嘛?辅助法官或律师提高搜集资料的效率、整合法律文件与对应的司法裁判、以及自动生成卷宗等等,都是一些机械的、重复的体力劳动。
然而,司法的核心不在于这些机械劳动,而在于法官在制定法或判例的约束下的法理衡量。或者这么说吧,司法不是机械地适用法律,而是在解释法律。法律条文看起来规定的很清楚,但其实歧义丛生、甚至有法律漏洞与立法错误。比如争议较大的“正当防卫”,“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什么是“必要限度”?每个案子中的“必要限度”都一样吗?如果没有普适的标准,法官如何去判断?这些问题就是司法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法律未经解释不得适用”,言下之意在于法律,司法也好学术也好,都不是在机械地盯着法律条文。“目光在规范与事实之间往返流转”(王泽鉴语)才是法律人最核心的工作。换句话说,法律人是在“价值判断”与“查明事实”之间做功课。人工智能能够辅助我们“查明事实”,但是“人工智能”所查明的事实对于案件是否有价值、如何选择这些事实等问题,依旧需要理性人的权衡。这个权衡过程人工智能是否可以进行?如果这些“权衡”只是定量地,那么或许可以,关键在于,司法并不只是定量分析,甚至定量分析都只是次要,定性才是主要。
民事诉讼不可能只是钱的问题,即便只是单纯的金钱债务纠纷,司法也要在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公序良俗之间权衡,而非机械地适用法条,更不用说民事诉讼中的重要部分婚姻家庭继承诉讼了,这更不是简单的钱的问题;刑事诉讼按题主说的确实简单,只是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犯罪论)、量刑、惩罚(刑罚论),但题主可能不知道,在刑法学界,这些问题是最让学者、律师、法官头痛的,因为说起来是一回事,但刑事诉讼是一个“定性”与“定量”皆有的过程。看事后的判决可能觉得简单,法条都说得很明白了,但那是因为法官已经经过细致、缜密地梳理与发掘,我们省略了大量的工作而已。
我们如何教会人工智能一件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到目前为止,人类依然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在司法中进行价值权衡,我们只是依据我们共有的、共通的道德感、正义感等等“基础规范”在进行权衡。然而,这些“基础规范”到底是什么?是否实在?是否可教导?这些问题,我们自己都没有答案。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确定的、稳定的对于“自由”、“公平”、“正义”、“善良”、“神圣”这些“基础规范”的概念,我们如何教导它们学会这些规范并在司法中运用?
也不是没有学者试着去除这些“法律宫殿中的神秘部分”,法律经济学的大佬波斯纳曾经也认为这些基础规范无用且累赘,主张用“社会最大福利”替代这些规范;但在与德沃金交锋数轮之后,他依然只能认输,承认这些规范的实在意义。
如果人工智能能够自主回答这些问题了,那也就不叫做“人工智能”了,因为它们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的认知范畴,并非“人工”所能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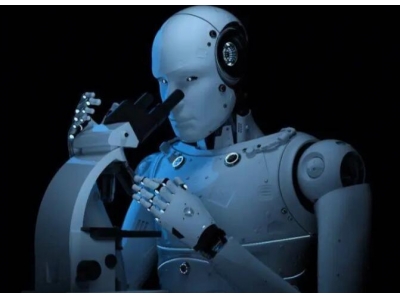 智能机器人为什么被称为“智能”机器人?2024-04-17 10:54:01一、智能机器人为什么被称为“智能”机器人? 智能机器人之所以叫智能机器人,这是因为它有相当发达的“大脑”。在脑中起作用的是中央计算机,这种...
智能机器人为什么被称为“智能”机器人?2024-04-17 10:54:01一、智能机器人为什么被称为“智能”机器人? 智能机器人之所以叫智能机器人,这是因为它有相当发达的“大脑”。在脑中起作用的是中央计算机,这种... -
 什么是人工智能2024-04-17 11:01:08一、什么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是当今科技领域的热门话题之一。它是指通过模拟人类智能行为的技术和方法,使计算机能够自主地执行任务、学习和做出决...
什么是人工智能2024-04-17 11:01:08一、什么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是当今科技领域的热门话题之一。它是指通过模拟人类智能行为的技术和方法,使计算机能够自主地执行任务、学习和做出决... -
 人工智能专业细分专业?2024-04-17 10:58:49一、人工智能专业细分专业? 1、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信息安全、物联网工程、数字媒体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空间信...
人工智能专业细分专业?2024-04-17 10:58:49一、人工智能专业细分专业? 1、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信息安全、物联网工程、数字媒体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空间信... -
 智慧农业专业要求?2024-04-17 10:49:16一、智慧农业专业要求? 智慧农业专业的要求首选科目要求包括:仅物理、仅历史、物理或历史均可3种。“仅物理”表示首选科目为物理的考生才可报考...
智慧农业专业要求?2024-04-17 10:49:16一、智慧农业专业要求? 智慧农业专业的要求首选科目要求包括:仅物理、仅历史、物理或历史均可3种。“仅物理”表示首选科目为物理的考生才可报考...



